外国学者热议中国新发展 |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至关重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至关重要——访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教授詹姆斯·K. 加尔布雷斯
当前,虽然有部分西方学者和媒体以错误的认知来判断中国,并对中国进行抹黑和抨击,但有更多西方学者坚持客观理性的学术立场,从事实出发,全面看待中国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林登·B. 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政府研究与商业关系教授詹姆斯·K. 加尔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h),请他分享自己对中国式现代化、西方的中国研究以及中美关系的见解。
20世纪80年代,加尔布雷斯担任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Joint Economic Committee)执行主任、副主任;1993—1997年,担任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前身)宏观经济改革首席技术顾问。加尔布雷斯的父亲是加拿大裔美籍经济学家、外交官,制度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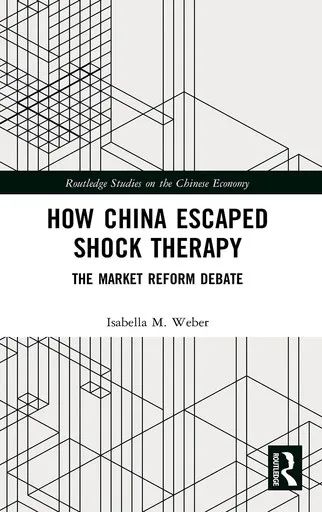
伊莎贝拉·韦伯 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 The Market Reform Debate(《中国是如何避免休克疗法的:市场改革辩论》)一书封面 资料图片
中国发展避免了西方模式和思维陷阱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担任宏观经济改革首席技术顾问期间有哪些工作体会以及学术思考?
加尔布雷斯:1993年,我参加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一个项目,担任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改革首席技术顾问,任期四年。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与我一起的还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各领域专家,包括人力资源、工业政策、宏观经济调控、国际经济政策等。我们的主要职责是以讲座、会议、考察团的形式为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及其他中国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政策参考。例如,在通货膨胀政策方面,我组织考察团前往巴西,访问20世纪80年代中期“非正统货币改革”政策(“heterodox monetary reform” policy)的设计者;在工业政策方面,我们前往韩国考察;在预算和货币政策监管方面,我们访问了美国国会的工作人员。受我邀请来到中国的学者包括美国新学院(The New School)经济学与政策分析教授、退休保障问题专家特蕾莎·吉拉杜奇(Teresa Ghilarducci),她介绍了美国社会保障系统的运作;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工资与就业动态中心主任迈克尔·赖希(Michael Reich),他介绍了独立工会(independent trade union)的社会功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荣休教授史蒂文·科恩(Stephen Cohen),他是法国工业政策方面的专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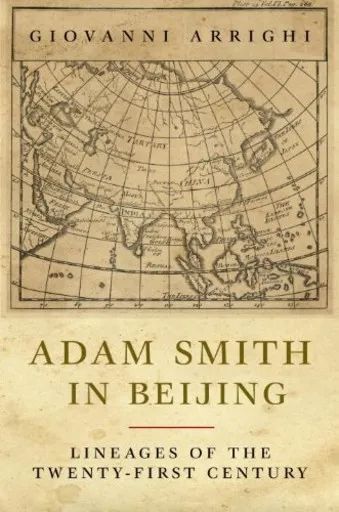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 世纪的谱系》(Adam Smith in Beijing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封面 资料图片
我可以谈谈对这个关键时期的几点深刻印象。
第一,中国的国家经济规划团队对讨论持极为开放的态度,从“自由市场”思想到传统的经济规划理论,在自己的工作中综合了各种各样的思想。这是最令我感到意外和耳目一新的。我也开始了解到,中国经济规划者对美国的经济规划举措做了大量调研,包括我父亲关于二战时期美国物价的研究。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系助理教授伊莎贝拉·韦伯(Isabella Weber)在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 The Market Reform Debate(《中国是如何避免休克疗法的:市场改革辩论》)一书中详细地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第二,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政府担心苏联的失败在中国重演,中国必须避免。我完全赞同这种观点。
第三,我在美国国会工作时见识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庞杂的规章制度。对比而言,中国中央权力机关的规模并不大也不复杂,特别是相对于国家规模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概念在西方与中国有着不同的含义。例如,“宏观经济管控”对美国人意味着货币和税收政策,而在当年的中国主要是指确保地方为中央提供充足的收入以支持中央政府的运转。我后来发表的一篇文章谈道,当年中国的改革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收入不足、预算赤字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风险驱动的。
第四,我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过去的成就为基础并从错误中学习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我一向提醒中国同事要避免这样一种思维陷阱:“发展”需要采取特定的西方模式或者新自由主义模式。1995年,我在北京怀柔组织了一场关于国际经济政策的会议,并邀请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艾斯纳(Robert Eisner)和曾担任美国众议院银行业和商业委员会经济学家的简·达里斯塔(Jane D’Arista)出席。我们不赞成中国取消资本管制,中国的确也没有这样做,我认为这是中国承受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这令我感到自己的工作对中国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城市公交车中的新能源汽车达到 46.6 万辆交车。
中国政府的主要关切一向是管理好本国事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加尔布雷斯:与西方相比,中国发展(不仅是在现代)的最显著特征可能是完全不存在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时期。中国发展的着眼点一直是在中国国内建立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而非外部征战。亚当·斯密在18世纪时就指出了这一点。意大利经济学家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也强调了这一观点。中国政府的主要关切一向是管理本国事务并预防他国干预中国事务,这是中国现代化极为突出和重要的一个特征。得益于此,中国社会和基础设施建设在和平年代快速发展。
自身过去的创伤也对中国发展历程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我属于同一代(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人经历过苦难,但他们也从中得到了非常多的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重要认识。我已经去世的岳母是中国人,他们那一代人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从过往的困难中学习是一种能力和力量源泉,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条件更好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如果遗忘关于过往的挣扎、奋斗的历程,是危险的。不过,就我遇到的中国人而言,他们对那些共同经历的记忆之深、受其影响之深,给我留下了极为鲜明的印象。
另外,新中国成立后在土地政策方面占据了优势。曾有一篇文章令我记忆犹新,该文称,新中国的土地政策深受19世纪美国经济学家、土地改革倡导者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影响。亨利·乔治认为几乎一切经济问题都源自“所有人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变为某些人的独有财产”,他主张推行单一土地税(single tax on land),即仅对处于天然状态、未被利用的土地征税。在他看来,土地的价值包含天然价值和使用价值(在土地上建造景观、建筑等),未被利用土地的价值来自对固定数量土地的需求,而不是土地所有者的牺牲或机会成本。由于未被利用土地的价值非劳动所得,对其征税不会影响生产性行为或土地供需关系,可以增加公共收入并减少经济不平等。
有能力将土地租金用于国家用途(尤其是在省、市层级上)是确保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成功的关键因素,而基础设施建设会引起土地租金上涨,形成良性循环。中国城市的发展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上述制度性事实对此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之外的大多数国家,土地租金是私有的,将土地闲置可以给投机者带来回报。据我所知,这种现象在中国是罕见的——中国城市没有荒废成为大面积的停车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有何意义?
加尔布雷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制度、资源基础和国际背景,我不倾向于总结规律。经济和社会模式未必具有普适性,当然在最普遍意义上与道德行为模式相关的部分除外。中国学者应对中国发展经验展开详细论述,以便为南方国家提供研究和实践参考,然后它们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回顾中国现代化历程,我有以下几点感想。第一,和平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冲突地带无法实现良好发展。第二,对金融活动的内部管控是发展进程长期稳定的关键。这需要将两方面结合起来:保持对本国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控制,并建立起牢靠、强有力的监管机制,后者对中国、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来说都是一项挑战。第三,国家需要储备训练有素的技术人才,如果人口科学文化素养低或健康水平堪忧,就很难取得成就。第四,制度多样性是一个优势,有助于促进建设性的竞争。第五,合理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避免交通、能源、供水等系统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当然,这要求依据合理可行的计划,设立牢固的机制以确保基础设施投资所需的资源可用。此外,当前有大量关于中国人口转型的讨论。中国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经历人口减少的大国,这是中国接下来要应对的重大挑战之一。
西方对华政策影响其学术话语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么看待西方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这些研究是否会对西方对华政策产生影响?
加尔布雷斯:除了少数特例,包括刚才提到的乔万尼·阿里吉、伊莎贝拉·韦伯,我对西方学术界的中国研究并不十分赞同。这些研究过分沉迷于意识形态争论,例如,中国式现代化是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成功案例,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案例?中国是通过采用西方规则还是打破西方规则(无论规则究竟是什么)取得成功的?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不太有价值,也无益于加深对中国的理解。一个可悲的事实是,现今一些西方学者仍在重复18、19世纪将中国“他者化”的习惯——将中国矮化为一种讽刺画(caricature),类似于老旧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比喻。这样做仅仅出于政治原因,且不具有建设性。
在我看来,西方对华政策一直以来根植于地缘政策考量,有时会利用或吸引学术讨论,目的是使出于其他原因制定的政策正当化。2001年12月27日,美国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即原来的最惠国待遇)。美国作出这一决定的驱动力是本国企业和银行寻求进入中国市场并在中国生产商品,而学术叙事将其合理化为“推进民主和自由”。如今,这种合理化调转方向,改为支持对中国抱有敌意的政策。一般来讲,政策影响着学术话语和公共话语的调性,而不是相反。这在宽泛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我对自己读到的大部分关于中国的研究持怀疑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式现代化是否给发展经济学、国际合作等领域带来新思路?
加尔布雷斯:西方“现存”的发展经济学起源于冷战时期,后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转化为应用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大体上聚焦于拉丁美洲、印度、撒哈拉以南非洲,对中国经验大多持漠然态度,西方专家一般也没有真正参与中国发展过程。因此,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更多的是中国问题专家而非发展经济学家的“专有活动”。当然,这扭曲了发展研究及其他相关领域的视角。
与中国正常经济关系的中断对美国是极大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现代化、制度改革、国家治理等宏大问题外,西方学术界研究当代中国的角度也日趋多元化,如现今有不少关于中国年轻人、中等收入阶层、网络文化等的研究。同时,中国正在多个领域内追赶世界领先水平,其国际影响力正在超出传统产业(例如纺织、钢铁),迈向高科技行业。西方学界对中国的新研究与中国自身的高速发展是否促使西方社会更新对中国的认识?
加尔布雷斯:对于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新角度,据我了解,近年来西方对中国社交媒体的讨论颇多。这些讨论集中于社会信用、内容审查、舆论管控等问题,大多以严厉苛刻的态度看待中国经验。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将中国与谁相比?在西方,由私营企业构筑的网络平台上同样存在审查、监视、管控现象,很难说这种比较是否合理。
在当下的美国,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很少。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彼时中国科技发展水平还不及西方,中美关系的基础是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在各类消费品制造行业,中国企业大量引进西方设计、西方标准,也进口了一定的西方机器设备,由它们生产或组装的产品进入西方国家和中国国内市场。记得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只有100多个汽车制造商(以西方国家或日本品牌为主)向中国出口汽车;那些专为中国市场生产的汽车产量小、成本高、质量不佳,且需缴纳高额关税。而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生产量最大的国家;在交通工程、先进电子元件、航天、通信等领域,中国也对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加之中国未完全开放金融市场,西方国家关键的经济部门自然将中国崛起视为威胁。
然而,如果现在中美经济关系脱钩,美国不可能不受到重创。中国的半导体进口量约占全球的一半,如果美国的先进半导体企业失去中国市场,就无法获得投资于半导体产业所需的巨额收入,由这些企业主导的高端设计过程也将崩塌。中国还是世界稀土储量最大的国家。稀土是重要的工业原材料,电子元件的制造离不开稀土,稀土对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也至关重要。
美国政府2021年6月就如何减轻美国供应链脆弱性发布报告《构建有韧性的供应链、复兴美国制造业并培育基础广泛的增长》,美国商务部、能源部、国防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分别撰写了报告主体章节“半导体制造与先进封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产与材料”“药物与药物活性成分”。虽然该报告仅重点考察了四类关键产品的供应链,也并不专门针对中国,但我们可以据此分析维护中美关系的必要性。
半导体产业是极度专业化、不间断的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和全球劳动分工的典范。美国主导设计和一体化生产,日本生产晶圆(wafer),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主攻高端制造,中国内地大量承担了中低端芯片生产及芯片封装。半导体供应链如同一个由许多独立节点组成的网络,每家企业可能只有一个上游供应商、一个下游客户,形成双边垄断(bilateral monopoly)。因此,链条上任何一处发生故障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中断。鉴于中国在半导体产业中的分量,即使是小冲突也可能立刻给美国造成大冲击。
就大容量电池而言,首要的供应链问题不在于科学驱动的设计和工程,而是关键原材料的获取。大容量电池产业发展的驱动力是电力储存需求,这个需求的一大来源是汽车产业。中国能够以低成本生产大容量电池在于中国自己就是第一大用户,中国和欧洲各消费了全球大容量电池产量的40%,美国仅占13%。2018年,全球共有425000辆电动公交车,其中421000辆在中国,仅有300辆在美国。对此,报告建议美国提振国内需求。“关键矿产与材料”一章列出了美国直接进口依赖度高于75%的38种矿产,其中18种的第一大供应国是中国。中国自身对这些材料有庞大的需求,能够从相应的供应链投资中获利;于是,全世界都选择这个大体量、低成本的生产者。
在每个领域,这份报告对中国的做法都持批判态度,公共投资、补贴本国企业、国家资助产业合理化、向消费者发放(电动汽车)补贴以刺激需求等国家规划被形容为“自上至下”“扭曲市场”。然而,报告对美国的建议以及美国政府的实际做法与它们批评的中国发展战略十分相似。例如,在锂离子电池方面,2021年3月美国总统拜登呼吁通过投资激发需求,包括推出1000亿美元的补贴以鼓励美国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对于半导体行业,报告建议美国联邦政府设置激励机制以推动新建或扩建半导体制造厂;美国《国防授权法》(NDAA)授权美国商务部为私营机构或公私合作机构提供经济援助,以支持半导体组装、测试、封装活动所需的设施建设、扩大和现代化。如此看来,中国和美国的激励措施究竟有何区别?报告并未给出清晰的解释。
基于上述思考,我得出几点结论。第一,在至关重要的经济领域,中美相互依存是不可废止的。与中国正常经济关系的中断对美国来说是极大的风险,这是客观现实。
第二,中国的优势在于务实的经济发展计划,包括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方面。中国幅员辽阔,能够充分利用规模化生产和广大的国内市场,在各个工业领域降低成本,这是其他国家难以效仿的;以社会稳定和增长稳定而非短期盈利和金融契约为导向的体制也起到了巩固作用。中国的优势是其成功发展道路的产物,这可追溯至新中国成立,建立起对国家土地和资源拥有完全控制权的中央政府。这些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也不是凭借诡计或不正当行为可以造就的。
第三,全球经济一体化不能被瓦解。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社会稳定、日益发达的国家,压制中国必将给世界带来破坏性后果。总而言之,即便中国与美国的相对地位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两国和平相处是更有利的选择。
责任编辑:牛淋淋


